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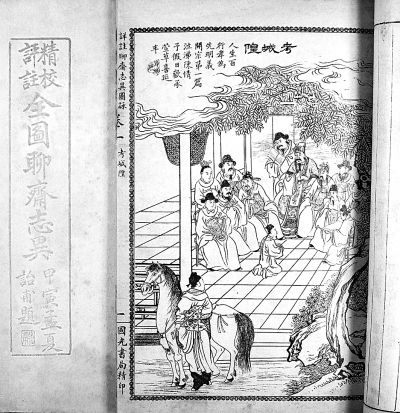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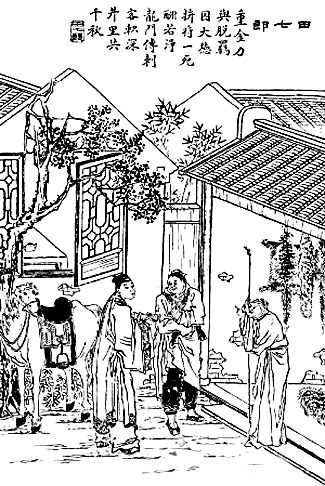
《聊齋志異》插圖
著名歷史學家李文海先生不幸因病於近日逝世,學界深感痛惜。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心系學術,筆耕不輟,殫精竭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去世前一天,他剛剛完成為《清史研究》撰寫的學術論文《〈聊齋志異〉描繪的官場百態》。長期以來,先生一直是光明日報的熱心讀者和重要作者,生前在本報史學專刊發表了大量膾炙人口、發人深思的精品佳作,深受讀者好評。經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及先生親屬協商,決定由本刊發表先生的這篇絕筆,以此作為對先生的緬懷和紀念。
——編者
郭沫若在蒲鬆齡故居聊齋堂上寫了這樣一副楹聯:“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這十六個字,簡明、精准地概括了《聊齋志異》這部文學巨著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
蒲鬆齡自己稱《聊齋志異》是一部“孤憤之書”(《聊齋自志》)。他通過談狐說鬼,講神論怪,宣泄和傾吐著自己對種種社會現實的滿腔悲憤。書中涉及的社會問題林林總總,而著力最多的,還是“刺貪刺虐”,對官場黑暗的無情揭露。
下面我們來看看蒲鬆齡筆下描繪的官場百態是一幅什麼樣的圖景。
“今日官宰半強寇”
蒲鬆齡在《聊齋志異》中曾經借一位姓徐的商人同“夜叉國”人的對話,討論了“官”是什麼的問題。“問:‘何以為官?’曰:‘出則輿馬,入則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諾﹔見者側目視,側足立﹔此名為官。”(卷三,《夜叉國》。以下凡引用《聊齋志異》者均隻注篇名)這裡對於官的描寫,主要強調了他們安富尊榮、威風八面、頤指氣使、睥睨群下的一面。那麼,這些聲名顯赫、位高權重的官員們的行徑和作為,又是怎樣的呢?
“老龍舡戶”講的是出沒於南海的一群江洋大盜,他們“以舟渡為名,賺客登舟,或投蒙藥,或燒悶香,致客沉迷不醒﹔而后剖腹納石,以沉水底”。但歷任有司,對報案者“竟置不問”,結果是“千裡行人,死不見尸,數客同游,全無音信,積案累累,莫可究詰。”直到朱徽蔭“巡撫粵東”,才把那些江洋大盜緝捕歸案,無數無頭公案得以昭雪。對此,蒲鬆齡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剖腹沉石,慘寃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絕不少關痛痒,豈特粵東之暗無天日哉!”“彼巍巍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心,尊優雖至,究何異於老龍舡戶哉!”(《老龍舡戶》)這段話講得很清楚,那些泥塑木雕一樣對百姓痛痒不聞不問的官員,雖然“出則刀戟橫路,入則蘭麝熏心”,冠冕堂皇,灸手可熱,其實同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沒有什麼區別。可惜的是,這樣暗無天日的政治,並不只是粵東一地,而是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成仙》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山東文登一位家道殷實的“周生”,因小事同“黃吏部”發生糾紛,黃仗勢串通邑宰,將周生家的仆人“重笞”一頓。周甚感不平,“欲往尋黃”。周的一位好友“成生”力勸之,說了下面這樣一段話:“強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把當時的官宰說成大半是不打旗號的強盜,由這些人來統治,世界當然就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可惜周生不聽,非要同邑宰去爭個曲直,結果惹惱了邑宰,不僅把他抓了起來,“搒掠酷慘”,“絕其飲食”,還賄迫監獄中的“海寇”,“使捏周同黨”,必欲置之於死地。在嚴刑逼供之下,“周已誣服論辟”,最后全靠著成生多方營救,才得以“朦朧題免”(《成仙》)。這是又一次把官員比作盜寇的例子。
在更多場合,蒲鬆齡常把那些殘民以逞的官員比作吃人的猛獸,悲憤地說:“竊嘆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為虎,而吏且將為狼,況有猛於虎者耶!”(《夢狼》)《三生》一文描寫了一位姓劉的孝廉,前生是縉紳之家,但“行多玷”,作惡頗多。死后始罰作馬,繼又罰作犬,最后則罰作蛇,“滿限復為人”。借這個故事,蒲鬆齡發了這樣一段議論:“毛角之儔,乃有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然者,王公大人之內,原未必無毛角者在其中也。”(《三生》)這篇文字不但暗示“王公大人”們如果作惡多端,難免變成犬馬之類,而且特別指出,其實“王公大人”之中,原本就有“毛角之儔”在。這段略顯隱晦的話,如果說得直白一點,無異直指某些“王公大人”不過是“人面獸心”的“衣冠禽獸”。
如所周知,《聊齋志異》寫狐,其實是在寫人。書中講了一狐仙,化作一位老翁,卻並不掩飾自己的身份,有人來訪,“無不傴僂接見”,“獨邑令求通,輒辭以故”。問其原因,回答說:“彼前身為驢,今雖儼為民上,乃飲米而醉者也。仆固異類,羞與為伍也。”(《濰水狐》)“飲而醉”是一個典故,原意是說,隻要有錢,即使不喝酒也醉了,也就是見錢眼開的意思。驢之為物,體大氣粗,表面威風凜凜,但扔給一點草料,也就“帖耳輯首”,實在同貪官的形象十分相像。所以蒲鬆齡評論說:“以此居民上,宜其飲而醉也。願臨民者,以驢為戒,而求齒於狐,則德日進矣。”這可以說是對前面“王公大人”中不乏“毛角之儔”的呼應。
《黑獸》敘述的故事十分簡單,講的是一隻老虎遇見一不知名的黑獸,竟觳觫戰栗,延頸就死的事。對此,蒲鬆齡發表議論:“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獼最畏狨﹔遙見之,則百十成群,羅而跪,無敢遁者。凝睛定息,聽狨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志顛頂。獼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狨揣志已,乃次第按石取食,余始閧散。余嘗謂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民之戢耳聽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黑獸》)獼和狨都是猿的一種。書中所說狨和獼的關系,是否合乎科學,我們不必深究,因為談論這種動物關系不過是一個由頭,要旨是從中引出官與民的關系來。上面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譴責“貪吏似狨”,對無拳無勇的“民”擇肥而噬,謀財害命﹔一是哀嘆小民們面對著“貪吏”的敲骨吸髓,狼吞虎咽,隻能“戢而聽食,莫敢喘息”。這既反映了對貪官污吏的強烈憤恨,也表達了對被欺壓、被凌辱的底層群眾的深切同情。字裡行間,充溢著對那些生存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處境下的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愴與無奈。這種鮮明的愛憎情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在是難能可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