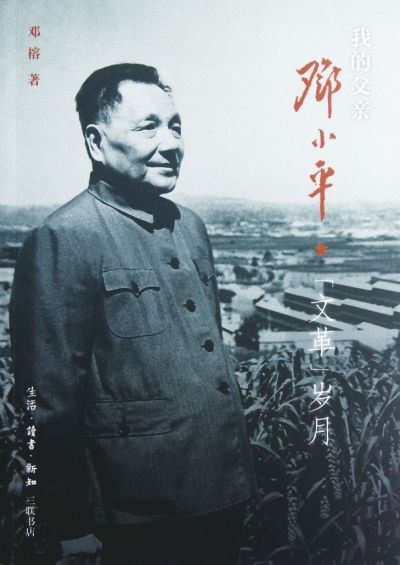
我们学着过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我们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共厕所,拿粮票到粮店买粮,凭本到煤厂买煤,过年过节的时候排队买木耳黄花和五香大料,一周一次四五点钟起大早去菜市场排队买豆腐。副食店里有大腔骨卖,院子里一招呼,赶紧拿着家伙和大家结伴而去。很快地,我们就学会了这种生活、熟悉了这种生活。人就是这样,只要心里头没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什么日子都能过,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况且,工人们就是这么过来着,比起他们来,我们还算“富裕”的呢。
这时,表面上,父母亲的工资仍然照发,不过钱由“组织”代管,发不到他们手里,要用时就得一次一次地申请。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家人,因无任何生活来源,中办规定,每个孩子每月发给二十五元生活费用,奶奶每月只有二十元钱,都从父母工资中扣除。每月的“月例”,中办指定专人送到中南海西门,由我们去领。在中南海里面,妈妈知道我们在外度日不易,总是找借口多要一点钱送给我们。她一会儿说冬天到了该买棉衣了,一会儿说被子没带够要买被子了,一会儿说男孩子能吃粮票不够了,每月总是想尽办法,变着法子,不管钱还是粮票,能多加一点算一点。在中南海外面,二姐邓楠和我每月按时去西门门口领钱领粮票。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夹在钱中妈妈手写的单子和纸条。拿着纸条,看着妈妈那熟悉而又秀丽的字迹,就好像触摸到她那温暖的双手,令我们激动而更加想念不已。时间长一点,我们的胆子也大了一点,开始以各种借口多要一点钱,还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要一些家中书房的书。一开始,对方态度不好,不搭理我们,姐姐和我就在中南海西门外大声地争喊,闹着不走,弄得对方无可奈何。由于我们不惧怕,敢和他们斗,妈妈在内,我们在外,相互配合,我们除了能够多领到一点钱粮之外,还从家里拿出来了许多的书。就是这些书,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以后无数个艰难孤独的日日夜夜。两年之中,在中南海的大墙内外,父母亲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唯一而又间接的方式,保持着仅有的一点联系。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我的奶奶。
奶奶名叫夏伯根,是父亲的继母,是我两个姑姑的母亲。她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位老船工的女儿,嫁给我的爷爷做续弦后,成为家庭成员中唯一的劳动力和生活支柱。在我们家乡,奶奶是方圆几十里地有名的能干人,她会做饭,会做农活,会做衣服,会养猪养鸡。爷爷早亡,留下孤儿寡母的一大家人,全靠她一人撑持。在国民党统治下,顶着“共产党家属”的罪名,她藏匿过父亲寄回家乡的革命书籍,保护过华蓥山共产党游击队的伤员,支持女儿参加当地地下党的活动。她心里认定一条,就是共产党好。1949年,四川刚一解放,奶奶把门一锁,拿着个小包袱卷儿就从家乡来到重庆,从此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奶奶来后,真是帮了妈妈大忙。由于工作忙,妈妈把家中的小事杂事全交给奶奶来管。我和弟弟飞飞都是奶奶带大的,后来我的两个姑姑的四个孩子也都是由奶奶带大的。奶奶不仅带我们长大,还给我们做饭做鞋做衣服。奶奶有一双小脚,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可是特别聪明,她会用心算算术,还每天听广播听新闻,国内国际大事儿差不多全都知道。我们长大一点儿后,她就教我们缝衣边儿钉纽扣儿,教我们腌萝卜做咸菜,教我们好多好多的生活常识。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我们从奶奶那里学到的东西,真是说之不完道之不尽。奶奶带大了这么多的孩子,操持了这么多的家务,爸爸妈妈总是说,奶奶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这次从中南海出来,父母亲不在身边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还有奶奶。奶奶原本就是劳动家庭出身,原本就在困难中度过了大半生,她什么都经历过,什么也不怕,什么也难不倒她。她虽不懂政治,但受到这么大的变动和冲击却没有慌乱。在方壶斋,街道上组织斗争她,她忍受着谩骂和侮辱,却一点儿都不怕。她凭着一股子硬气劲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倒要看看怎么个结束!”有了她,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是我和飞飞,就有了生活的依靠。有了她,我们才可能比较快和比较容易地渡过难关。我们周围也有许许多多被赶出家门的“黑帮子女”,其中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没有生活技能和生活经验,不会生火,不会做饭,不会管理钱物。有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人衣裳破了不会补,有的人住的小屋又破又脏又乱。而我们,则有奶奶,有这最后的依靠。其实,奶奶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依靠,而且还是最为可贵的精神支柱。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奶奶,我们怎能如此顺利地适应生活?可能连“滚出中南海”后的第一顿饭都没有着落。奶奶不仅照顾我们这一家人的生活,还特别富有同情心。罗瑞卿家的玉田、朵朵和点点,乌兰夫家的其其格几个女孩儿,也都和奶奶特别的亲。她们都是被赶出来没有家的孩子,偶尔来我们家或住我们家时,都是奶奶给她们做饭吃。在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心中,奶奶,是大家的奶奶。
到方壶斋后,我们尽管仍可从父母那里领来一些生活费用,但由于不知道这种状况能够维持多久,不知以后还会遇到什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尽量节俭度日。奶奶特别会做饭,也特别会节省。炒菜虽然没肉少油,但放点儿她自己做的豆瓣辣酱,就香味四溢。买来腔骨,炖一大锅,可以做菜,可以煮面,也可以做汤。炸一碗酱,肉少点,酱多点,再买点切面(粮店里卖的新鲜面条),放点自制辣椒油,炸酱面的味道就自然不同。飞飞十六岁,在蹿个儿,正是能吃的时候。奶奶心疼小孙子,有时想给他做点肉菜,可飞飞不吃,说就爱吃炸酱面,有一段时间甚至故意天天吃、顿顿吃,足足吃了一个礼拜。
奶奶、飞飞和我在家里住着,过得总算安稳。而哥哥姐姐们却还得回所在的大学接受批判和管制,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大姐邓林被中央美术学院造反派关起来。院内院外只要一有事件发生,也不管与她有关无关,都要把她拉出来斗一番,斗别人时,也要让她“陪斗”。大姐是个老实的人,对造反派的审讯和谩骂,她不会回嘴,不会争吵,只坚持一条,就是不管问什么,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造反派让她“劳动改造”,美院所有的女厕所都让她一个人打扫。她每天兢兢业业,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她特别想家,担心在家的奶奶和弟妹。每次我去看她,她都问个不停,总想多说一会儿话,舍不得让我走。哥哥朴方在学校被造反派限制了自由,不能回家。他想念亲人,就和同在北大上学的妹妹邓楠约好,每个星期悄悄地在未名湖见面。未名湖畔,兄妹两人趁着晚上天黑看不见人,避开造反派的监视,畅开胸怀,相互交换消息和想法。哥哥对历史和政治知道得多,对形势也比较敏感,他给妹妹讲了好多对局势的分析。而妹妹则可以出学校可以回家,外面的消息多一些,也趁此时全部告诉哥哥。已经记不清楚在未名湖畔共有多少次见面了,只记得从小到大,兄妹之间,从未如此深地在思想上相互沟通过。
邓楠在学校虽也受到批判,但造反派允许她周末可以回家。她数学好,又会算计,所以我们那个在方壶斋的家,就由她全权管钱管家。可以说,在那两年中,对家里和弟妹操心最多的就数她了。每次从学校回家,她总要买点东西带回来。想买点水果带给弟妹,又嫌贵买不起。平时香蕉三毛二分钱一斤,偶尔可以碰到一毛二分一斤的处理品,便高兴极了,有点儿烂也没关系,赶紧买点给大家“解解馋”。有一次她看到卖旧木板子,就买了几大块,走了好远的路,累得呼哧呼哧地扛回家来。别看木板旧,买回来还真有用,后来哥哥拿这些木板,为家里做了一个小碗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