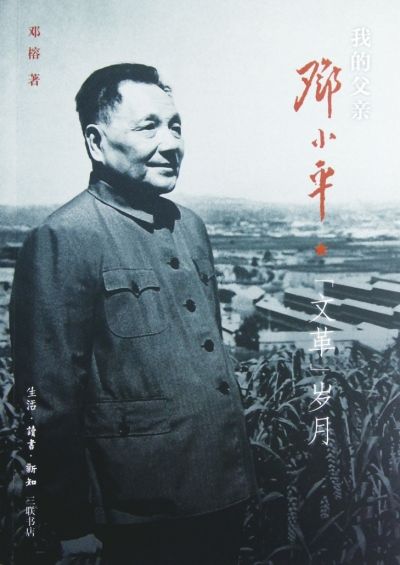
到了晚上,院子寂静漆黑。空荡荡的房间里,只点一盏昏暗的小灯。父亲无言无语,闷坐抽烟。母亲先是看着他抽,后来也跟着抽了起来。为了节省,她只捡父亲抽剩下的半截烟抽。父亲知道母亲心脏不好,劝她不要抽,说:“现在你的烟瘾比我还大,将来怎么办?”母亲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们。只要能见到他们,我马上就不抽了。”
这种囚禁的生活虽然难过,但庆幸的是,他们总算没有像别的“走资派”那样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残。
父亲没有受到其他“走资派”所受的迫害和虐待,并不是什么侥幸。还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原因,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安排。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在对其批判打倒的同时,在政治上是有所保留的,在人身上也是保护的。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到了1967年11月5日,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毛泽东虽然仍把邓小平与刘少奇联系起来,错误地批道:“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把刘、邓拆开来。”
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明面上,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的决定,而在深层次上,涉及的问题则是既多又复杂。
毛泽东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公开场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在私下里,在私人之间,毛泽东却似乎从未与林彪“亲密无间”,这是为什么?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这又是为什么?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难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林彪最“红”的时候,毛泽东就想到了什么,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什么?毛泽东之心,实如大海之深,深不可测啊。
按照毛泽东的预言,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的事情,的确是又多又快又混乱。
继“一月夺权”和“二月逆流”之后,3月,掀起全国范围“抓叛徒”的风潮,无数无辜者被诬蔑和定罪。4月,报刊上对刘、邓,特别对刘少奇的批判大大升级。6月,打、砸、抢、抄、抓的歪风泛滥全国,中央不得不发出进行纠正的通知。7月,林彪提出抓“军内一小撮”,一大批军队干部被打倒。同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致使全国各地武斗急剧升级,大规模流血事件频频发生。8月,在中央文革煽动下,发生了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涉外事件。
到了这时,全国上下,包括军队的各级干部大批倒台,党和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各派造反组织相互争斗,大规模流血武斗不断爆发,工农业生产被严重破坏,生产持续下降,全国陷入大动乱和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毛泽东从7月到9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巡视之后,他非但丝毫没有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反而发表谈话说:“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他的预言实现,看到了真正的“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既然要乱,就要彻底地乱,翻天覆地地乱。
毛泽东曾经自我剖析:“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虎气,是王者之气,是霸道之气;猴气,是斗争之气,是造反之气。集此二气于一身的毛泽东,极其典型地融合了因二气而造就的双重性格。他既是主宰者,又是造反者。他以主宰者的身份,发动了造反运动;又以造反者的身份,达到了新的主宰境界。环顾古今中外,毛泽东,只有毛泽东,可以以这样不同寻常的性格和方式,去造就和追寻他那不断“革命”的理想。
毛泽东是一个伟人,是一个永远的强者。他的所想所为,不可以常人而论之。也许,这就是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常常会出现巨大的差距的原因之一。
第8章
狂涛中的一叶孤舟
在为“文革”所冲击的芸芸众生中,我们家的命运,并不是最悲惨的。父母亲姑且不论,因为他们是政治人物,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上的浮沉本就是他们的“宿命”。但是,对于我们,这几个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来说,从极其单纯的学生生活,一下子落入被批斗被污辱的万丈深渊,的确是艰难的人生体验。
从中南海被撵出来后,中办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胡同里给我们找了一个住处。那是一个院子,除了一些简陋的平房外,还有一栋据说是日伪时期建的小楼。在一楼的最里面,给了我们两间房子。院子里住的都是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还有个别中办内部“犯错误”干部的家属。我们搬来以后,奶奶和我的弟弟飞飞住一间,我们姐妹三个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表姐住一间。这个楼房已很破旧,木板地一走就咯吱咯吱地响。我们的住房和隔壁只一板相隔,那边的人咳嗽一下都清晰可闻。楼外院子中间有一个水龙头可以打水,厕所则在院外的街上。我们在走道里支上新买来的炉子,用冒着烟的木屑引着了煤火,奶奶为我们做了在这个新家中的第一顿饭。
把家安顿好后,我们感到十分庆幸。庆幸我们没有像刘少奇家的孩子一样被赶到学校,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回的家。这个家虽然简陋,但它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斗争得来的。当一切安顿下来,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挤在木板搭的床上,久久不能安睡。我们想念我们的父亲,想念我们的母亲。我们知道,此夜此时,他们一定也不能入睡,一定也在想念着我们。
中南海不管怎么样,仍是一个“世外桃源”。到了方壶斋,则就真正到了社会上了。
院子里住的都是中办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可能上面有交待,因此对我们都还不错。看我们刚来,还来问我们缺什么少什么,或给我们送点葱送点酱什么的。从中南海的家乍来这里,我们觉得破旧而简陋,但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则从来就住在这里,从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从来也没有觉得不好。来到这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工人的工资极少,最低的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元,多的也不过四十来元,还要养活老少三代一家子人。一些工人家属靠糊纸盒子或火柴盒挣钱补贴家用。有的工人家中连个正式的床都没有,两个长条凳搭个大木板,一家子人就睡在上面。吃饭也就是棒子面窝头加咸菜,带肉的炸酱面就是好东西了。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特别是那些小孩,能遮着盖着不冻着就不错了。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