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原
2014年06月24日08:5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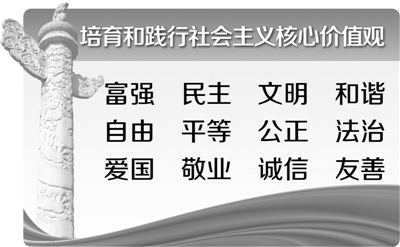 |
|
|
与汝信(见上图。资料照片)交谈,你会感觉无拘无束。这位耄耋之年的著名学者面容清癯,言语平和,什么复杂的道理,在他那里都浅显易懂;什么艰难的往事,在他的视野中都只是一种自然经历。
他成长在上海,家境富裕,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一口流利的英文,但他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后来投笔从戎,还在朝鲜战场出生入死整整5年半;他研究的是西方哲学,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领导职务,但繁重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与他的哲思互不冲突。熟悉汝信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奇才,行事游刃有余,研究融会贯通,“什么都难不倒他”。
自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无论研究什么,不管写到哪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他治学的指南。2004年,他被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还参与编写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百次审议会议中,他每次都有所建议。“在他的身上,我们年轻一代看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学人的修养和执著。”工程办公室的几位青年工作人员这样认为。
■“战争的考验,让我后来可以坦然面对一切起伏和荣辱”
说起身在上海地下党的那段岁月,汝信仿佛又回到了青春时光。“其实,当时在上海,有许多大学生都怀抱理想,投身学生运动,纷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我只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汝信所说的这些学生地下党员中有很多人成为各个领域的青年才俊,改革开放后又大多成为各行业的领导干部或学术领军人物。汝信则成为哲学名人。
在党的外围组织读书联谊会中,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入党后又从秘密渠道阅读了来自解放区的各类读物,包括毛泽东的著作。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里,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解放大军开进上海,这位圣约翰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对新中国充满憧憬,先是参加护厂护校,后又参与社会调查;当大军南下急需干部时,他又意气风发地入伍,可部队尚未开拔,便接获命令,赴朝参战。“我们连冬装都来不及换,就匆匆登车北上,在车站临时停车时才下车换装。”回想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汝信感受到的是人生车轮急速飞转,“真是党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汝信的英语水平很快就派上了用场,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转入司令部当英语翻译,每天面对一拨拨俘虏,他要甄别身份,搜集情报,一介文弱书生迅速锻炼成勇敢的战士。在炮火硝烟中穿行,天天由这个坑道跃进那个坑道,他经历了从第二次战役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的全过程,不但当过翻译,还在作战处、情报处任参谋,做过王必成将军的秘书,司令部的各类工作几乎都轮了个遍。“炸弹就在身旁爆炸,有的战友牺牲了,一位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倒下了,但我的意志更坚定了,这就是战争的考验,让我后来可以坦然面对一切起伏和荣辱。”
在汝信的经历中有许多学术探索都是时代促成的,凭着他的勤奋和领悟,又结出了累累硕果。在上海读书时,因为要阅读社会主义理论,他开始自修俄文,奔赴朝鲜战场途中,经过沈阳的国际书店,他买了本俄文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从此,这本书成为他提高俄文阅读水平的基础教材。战斗之余不忘学习,躺在坑道里仍在捧读,不仅让他回国后写出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述,还曾临时上阵,当起了俄文翻译。
从朝鲜战场回到祖国,他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在院部工作;1956年随团赴苏联考察,没料到原定的翻译缺席,全团只有他对俄文还略知一二,就被大家推举为临时翻译。“我的口语那时还不行,结果洋相不断,记得最深的一次是苏联专家说集体宿舍,我怎么也听不懂,他就画了间房子,里面还有床,我一下就明白了。”这个故事在汝信的口中是玩笑,但却说明,在实践中学习,在工作中积累,是汝信学术思想的特征。
■“马克思虽然没有写过系统的美学专著,但在美学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上个世纪50和60年代,全国上下都在学哲学、用哲学。汝信很幸运,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追随著名学者贺麟读副博士研究生,虽说后来副博士这个学位不再使用,但他却从此深入研读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对黑格尔有独到心得。他还将西方哲学一一梳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了然于胸。
研读西方美学史的人都不会忘记,1963年,《西方美学史论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汝信的第一部代表作,与20年后出版的续编一起,已成为美学研究的必读。汝信在专著中,对古希腊以来直到20世纪初期的西方重要美学家逐一分析,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他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写过系统的美学专著,但在美学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因为马克思把美学现象放到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整体中去考察,和现实人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与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从而从根本上突破了以往传统美学的框架。
汝信不仅对西方哲学了如指掌,还对中国哲学素有研究,可谓学贯中西。汝信回忆说,这也是时代造就的结果。那时,任继愈受毛主席和周总理之托,研究世界宗教,还主持编写中国哲学史,任继愈点名邀请汝信参与。任继愈认为,如果都是中国哲学的专家参与,思路就难以拓宽,所以一定要有汝信这样的外国哲学人才加入。汝信因此又系统研究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汝信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对周谷城、贺麟、朱光潜、任继愈等前辈大师的言传身教念念不忘。尤其是贺麟和朱光潜两位老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精细研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贺麟还在81岁高龄时入党,更令他感慨不已……
■“他始终在求索,一直在开创,不断在思考”
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汝信回顾近70年的寻美求真之路,对此感悟颇深。
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哲学曾长期活跃在风口浪尖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更是名重一时。汝信在做学问的同时,不断撰写文章,参加写作班子,还曾住在人民日报的招待所里写出一篇篇讨论哲学的文字,投入思想论战。所有这些,加上中国发展道路的坎坷不平、理论建树的风风雨雨,让他逐渐认清了许多问题,对他80年代以后的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汝信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全面研究了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带着10多麻袋哲学书籍回国后,他很快就写出《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等文章,立即引发热烈讨论。他为博士生周国平的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作序,其中说道:“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序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轰动一时。全面分析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使他从新的角度认识了人。
《美的找寻》是汝信写的美学散记,多次再版,而且被很多人所珍藏,反复阅读。这部名作,文字晓畅优美,从绘画、雕塑到芭蕾、戏剧,无不涉猎。在莎士比亚故乡看《麦克白斯》《吃土豆的人》对社会的启示、罗丹博物馆的观后感、毕加索的再探索、《天鹅湖》的结尾和莎乐美的爱,读者随着作者在找寻美的过程中开启了心智。用散文的形式来探讨美,是汝信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想法,他始终认为,美学一定要与社会相联系,让更多的人去领悟,不然,美学就失去了社会意义。“美就在我们面前,美就在我们的生活里。”2007年12月,他在再版序言里这样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汝信又踏进了新的领域——世界文明对话。1994年起,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数十位学者聚集一堂,将目光投入到世界各地,编撰出版了《世界文明大系》《世界文明通论》等,还组织了一次次国际学术会议,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他始终在求索,一直在开创,不断在思考。”听过他的课、读过他的书、关注他的学生和学者这样评价他。
“以人为本”,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经过数十年哲学讨论的大风大浪,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的见证人,汝信深感“以人为本”的来之不易。近些年,他多次在大学讲堂上对后辈学子阐述以人为本的由来,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殷殷期望。
“回顾自己的探索过程,经验教训不少,成果实在不多。”汝信对自己的学术生涯经常反思,谦逊之情每每自然流露……其实,汝信就是20世纪后半叶我国美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读美学,离不开读汝信。
《 人民日报 》( 2014年06月24日 06 版)
| 相关专题 |
| · 热点·视点·观点 |

微信“扫一扫”添加“学习微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