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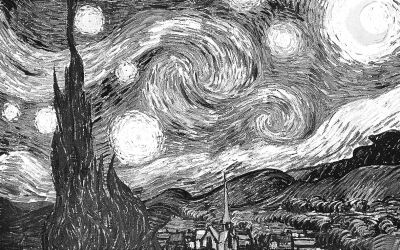
資料圖片
盡管我們比過去無數世紀的人類更了解自己所處的世界,但今天的科學研究還充滿了許多的未知供人們想象,這種想象在很多方面激發了科學更持久的發展,同時也給藝術創作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太空美術”就是我們對於肉眼不可視空間的一種視覺再現,是天文知識和人類對宇宙美好幻想在畫布上的重現。
天文科學與美術的融合
“太空美術”一詞由美國當代著名的太空美術畫家米勒在1978年出版的《太空美術》一書中倡導和推廣。1990年,曾是國際天文美術家協會主席的英國著名太空畫家哈代在《太空美景中》介紹了全球幾十位太空畫家及其代表作,充分展示了太空美術的現狀,以及這些作品表現的壯麗太空景觀。
在展現太空美景的作品中,隨處可見“科學”,比如美國藝術家邦艾斯泰的《水星天空的太陽》,我們可以看到明亮的光球和太陽黑子,色球層和紅色日餌以及太陽外圍銀色日冕形,非常富有魅力,太陽右下方的一簇小星是美麗的七姊妹星團。這樣具有高度准確性的作品,是和天文科學的發展分不開的。
宇航科學也是太空美術常見的題材。日本畫家岩崎一彰的作品《阿波羅II號歸來》描寫了1969年三名宇航員駕駛飛船,在進入大氣層后因為快速摩擦而發光發熱的場景。
另外一類太空美術作品對宇宙中各種人類不可視的場景進行想象,可以稱為太空科幻美術。中國著名太空美術家喻京川認為,它描繪人類未來的各種太空活動及太空壯舉,具有預測性,其描繪的世界可能實現,也可能無法實現,但它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
科幻和科技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比如凡而納在《海底兩萬裡》中暢想了可水下運行的船,稱之為“鸚鵡螺”號。1801年,第一艘由富爾頓所制的鐵質潛水艇下水,為向凡爾納致敬,其被命名為“鸚鵡螺”號。科學幻想與科技發展的緊密聯系可見一斑。從這個角度來說,太空科幻美術的魅力正在於你不知道未來是什麼,而你正在創造未來。
還有一類太空意向美術作品,是以太空為題材進行純幻想描寫的美術。這類作品最大的特點是表現精神的無序和跳躍,它可以拋開一切理性的束縛,盡情表達作者的各種情感、思想。
比如前蘇聯美術家卡拉耶夫的《宇宙生態》,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宇宙浩瀚和星光的璀璨,但並非通過具象描寫獲得,而是一種情感共鳴。這是對太空科學的情感解讀而不是景色解讀,但它依然建立在人們對太空不斷探索和理解的基礎上。
科學想象無法被替代
太空攝影作為太空影像的一部分,對今天的太空研究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把太空的絢麗展示給公眾。
然而,太空攝影和太空美術仍具有不可相互替代性。不論攝影師的技巧多麼高深,太空攝影記錄的影像“摹本”都是要受到客觀“原型”的限制的。而科學技術的發展有時是需要想象的,太空科學亦如此,而想象的部分,恰是攝影無法做到的。
比如宇宙大爆炸,這樣的天文現象和場景隻存在於推理、想象中,這種想象對於科學的發展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現代天文學中的很多理論都與此有關。但在所有的太空攝影作品中,不論是側重攝影的“工具性”還是“審美性”的作品,都無法展示出這一場景。而太空美術在描繪這樣的天文場景中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些作品帶給公眾的是具體的景象,通過畫家的“翻譯”,公眾可以相對直觀地“看到”科學家推想的場景。正如本雅明所說:“藝術的基本任務之一始終是創造一個尚不能完全滿足的要求”。
另一方面,正是攝影術的出現促進了“太空美術”的發展。在1893年攝影術誕生之前的兩百多年裡,科學家們運用圖畫的方式記錄太空的景象,這種太空寫生資料可以說是太空美術的前身。1609年,隨著望遠鏡技術的不斷改進,人類對於太空的認識越來越豐富。很快人類歷史上第一幅天體素描寫生《月面圖》誕生了,人們開始用更加理性的目光審視這迷人的星空。然而,這種以科學研究和科學記錄為目的的太空寫生資料並不是太空美術,這種理性的資料圖片很快就因為攝影術的出現而被替代。
攝影術的出現對以求“像”為主的古典繪畫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十九世紀西方繪畫的巨變與攝影術的出現是分不開的。在以梵高、修拉、高更、塞尚為代表的后印象派,尤其在塞尚的作品中,出現了一個主體創造和主體體現的自足獨立的藝術世界,這標志著自由意志主體取得了支配性地位,藝術成為他的構成物。這種趨向抽象的藝術意志拋棄了對自然物象的模仿和依賴。藝術家的審美經驗、感受、情緒成為繪畫的主要部分被充分放大,出現了西方美術中的所謂“表現”。太空美術的出現也是在太空攝影的沖擊下、在太空寫生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一種藝術形式。
包裹科學的生硬
哈代說過:“公眾或許難以接受很多實際的論據,但卻可以接受太空美術作品。太空美術在公眾與那些從實驗室和觀測中得出的抽象的難以理解的數據、理論、符號之間起到橋梁作用。”也就是說太空美術可以通過圖畫的方式,把科學知識直觀化和簡單化,有助於受眾的理解。比如銀河系的形狀,在天文學中,即便是這種簡單的知識,要用文字的形式傳播給公眾也非常困難,公眾對晦澀的科學術語和文字的忍耐力極其有限。借助太空美術,即使不做太多的解釋和說明公眾也能理解。比如太陽系中諸星球之間的關系、比如宇宙的誕生或毀滅等。
太空中並不都是美好的圖景,也存在黑暗、空曠。藝術家能賦予星球不同的絢麗色彩。這似乎使科學知識的准確性打了折扣,但當某些科學知識過於抽象時,卻可以起到幫助傳播的作用,這可以加深公眾對科學知識的理解,不能因其描繪的對象與真實的自然之間存在差異就認為它失去作用。
太空美術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它還是藝術家情感表達的載體。不論是哪種形式的作品,我們都可以看出藝術家對於太空及人類航天事業的情感,或者熱愛、或者擔憂、或者自傲、或者充滿敬意。藝術家通過視覺傳達,希望能夠引起受眾對這種情感的共鳴。有了這種情感的共鳴才會增加對太空的關心和熱愛。這正是科學文化傳播的重要方式之一。
太空美術作為新時代美術中的一個重要題材領域,其作品既反映了太空時代的科學成就,又反映人類對自身現在及將來進入太空世界的各自思考,並且加以深刻的揭示。美國天文學家兼太空畫家哈特曼自豪地寫道:“在人類科學技術的力量到達之前,我們已經到達了那些星球世界”。太空美術除了把知識圖像化,更重要的是把知識感情化和藝術化,包裹科學的生硬和理性,激發人們對科學的情感。
(詹琰 作者單位: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
鏈接
梵·高的《星夜》與“渦狀星系”
荷蘭后印象派畫壇巨匠梵·高在1898年繪制了名作《星夜》。對於位於畫作中央的漩渦到底為何物,后世有不同解讀。近日,一位美國藝術家提出新証據,認為梵·高其實在描繪離地球有2300萬光年的“渦狀星系”。
這位藝術家發現英國天文學家威廉·帕森思手繪的一張渦狀星系圖和梵·高的《星夜》裡所畫的呈螺旋狀上升的星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威廉·帕森思出生於1800年,他制造了當時最大的天文望遠鏡,並用這個望遠鏡觀測渦狀星系M51,於1845年完成首幅描繪該星系的圖畫,梵·高的《星夜》比威廉·帕森思完成這幅手稿晚了數十年。
這位美國藝術家推測,梵·高應是在巴黎或法國南部聖雷米精神病院休養期間,在圖書館接觸到這幅渦狀星系的畫作,而這畫作給梵·高留下深刻印象,並以此作為繪畫《星夜》的題材。
此前,專家對於《星夜》表達的背景及含義眾說紛紜。有藝術家指畫作反映梵·高的精神狀態不穩,那些巨大的、卷曲旋轉的星雲是畫家在幻覺和暈眩中所見,但亦有物理學家指梵·高是在繪畫星系。此次的發現,或許能給《星夜》的解讀帶來新的確鑿証據,若梵·高果真是在描繪“渦狀星系”,那麼《星夜》從某種意義上講,也算得上是一幅太空美術作品了。

| 相關專題 |
| · 熱點·視點·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