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盧曉琳
2016年12月13日08:07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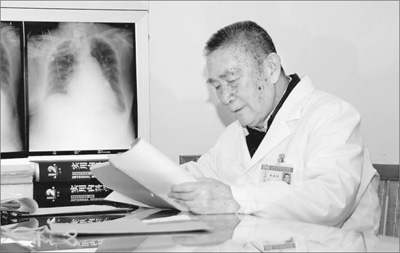 |
|
|
編者按:在百姓眼中,他們是一個個慈眉善目、妙手回春的好大夫﹔在同行眼中,他們是醫學泰斗,是一座座讓人仰視嘆服的“山峰”﹔但他們最本色的身份是共和國軍人、優秀的共產黨員。
他們,就是解放軍總醫院的四位百歲軍醫:老年醫學專家牟善初、口腔醫學專家周繼林、胸心外科專家蘇鴻熙、婦產科專家葉惠方。他們,是守護黎民蒼生的大醫,是八一軍徽上閃耀的光芒,是黨旗上鮮亮的霞光。
四位百歲老軍醫、老黨員均經歷新舊兩個時代,革命戰爭時期不懼險阻投身民族解放事業,新中國成立后積極投身興國大業,遭受坎坷挫折仍堅守初心,退休多年依然躬身治病救人一線,以身垂范對黨一生追隨、對事業不懈追求、對病人大愛仁心,唱響了人民軍醫忠於黨的信仰之歌。
從今天起,本報連續刊登通訊,帶您走近解放軍總醫院四位百歲軍醫的光輝歲月。
“醫德第一,醫術深通,口碑載道,舉世崇敬。”國學大師季羨林曾這樣評價牟善初(上圖,資料照片)。
作為我國老年醫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學貫中西的大內科專家、臨床藥理學家,牟善初創建了我軍第一個老年醫學研究室,是我國醫學超聲波早期應用的倡導者,在復雜心血管病診治、嚴重肺部感染的抗生素應用、老年多臟器功能衰竭救治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詣。他最早發現慶大霉素的腎毒性,提出老年腎功能損害的病人應絕對禁用慶大霉素的論點﹔他是我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開拓者之一,總結出一整套防治措施在全國推廣,為消滅血吸虫病作出重大貢獻。
牟善初是醫林參天樹,卻說自己離不開病人,“我與患者就像大樹對泥土的情誼”。牟善初醫高為師,但正如他的名字一樣,他善懷如初,永葆醫者仁心。
是醫者,更是一名軍人
——“一心報國,服務人民”
牟善初,是醫者,更是一名軍人。軍人本色是他身上最鮮亮、最深沉的底色。走過世紀年華的牟善初用一生詮釋了一心向黨、赤誠報國的如磐信念。
1917年,牟善初出生在山東日照一個農耕家庭。1943年,牟善初從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畢業,當時畢業生有“軍用”和“民用”兩個去向,自己抓鬮決定選擇哪一個。牟善初抓到了“民用”,這讓立下“奔赴戰場,驅趕日寇,還我河山”志向的牟善初非常失望﹔恰好一位抓到“軍用”的同學因種種原因不能從軍,於是二人私下進行了調換。第二年,牟善初如願奔赴雲南騰沖抗日前線,當上了手術隊上尉軍醫,在炮火紛飛的戰場上,他和戰友們搶救了一個又一個抗日軍人的生命。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虫何?”毛澤東《送瘟神》詩句中的小虫,學名血吸虫,血吸虫病被稱為“瘟神”。1950年,牟善初受命出征這場圍剿“瘟神”的戰役,擔任某防治站副站長。牟善初通過反復實驗,將治療血吸虫病的銻劑使用天數由原來的21天減少到6天,明顯降低了銻劑藥品的毒副作用,形成了一個快速有效的預防和治療方案。血吸虫在牟善初和廣大醫務人員面前終於敗下陣來——越來越多的村民得以康復,越來越多的農田得以復耕。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牟善初滿懷對祖國醫學事業的熱愛,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醫學人才。
1974年,牟善初調入解放軍總醫院工作。該院老年心內科名譽主任葉平深感牟老為祖國醫學事業培育人才的赤誠之心,“牟老指導過無數學生的論文,無論多忙都對論文仔細修改和把關,但從不在文章中署名第一作者,他說要多把機會讓給年輕人。”健康管理研究院主任曾強這樣描述牟善初對學生的指導:“實驗數據若有不准確,必須重算﹔實驗動物缺失一隻,必得補齊﹔論文中的每一個英文單詞他都細心校正。”老年腎內科主任程慶礫在美國留學期間,牟善初每個月給他寫一封信詢問學習和生活,鼓勵他學成回國工作。
走進牟善初工作了近半個世紀的總醫院,已是百歲高齡的牟善初躺在病榻上,雖然精神不如往昔,但牟老一字一句地說:“人貴有志,奮力前行。不畏艱險,莫相攀比。一心報國,服務人民。”他微笑著,真摯、慈祥。
95歲前,每天8點准時上班
——“病人有事,隨時叫我”
我國隋唐名醫孫思邈曾雲:“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
視患如親,待患如初,牟善初身上的醫者底色閃耀著醫者的光芒,從未褪去。牟善初的學生、解放軍總醫院老年心內科主任醫師李小鷹永遠忘不了1992年春節前的一次搶救。患者因肺心病心力衰竭,憋喘明顯,經過幾個小時的搶救仍無明顯起色。血生化和動脈血氣報告提示,復雜的酸鹼平衡紊亂可能是重要誘因。心中沒有把握的李小鷹撥通了牟善初家的電話,時已深夜兩點鐘,窗外大風卷著漫天雪花肆虐。“我馬上就來。”牟善初在電話裡說。當病區的電梯門打開時,李小鷹仿佛看到了“聖誕老人”:75歲的牟善初大步跨出電梯,羽絨服上落了一層厚厚的雪花,急切出門都沒來得及換上棉鞋的牟善初,腳上的一雙布鞋已然濕透。“老師見我第一句話是,‘病人怎麼樣了?’他仔細檢查完病人后就指導我們搶救,直到病情穩定下來,就這樣守在病房一夜。”東方泛白,面色蒼白的牟善初走出病房時說:“病人有事,隨時叫我!小鷹你要記住,搶救是最好的學習,從搶救中學習,不斷更新自己!”
患者為重的醫者底色從牟善初傳遞給了一代代后來人。“在此后的十幾年中,我也曾無數次因病人的病情被呼叫過,我一次都沒有延誤過。偶爾想偷懶時,牟老師的教誨就在我耳畔回響……”李小鷹告訴記者。
令老年腎內科護士長張瑞芹非常震撼的是,牟善初一直到95歲前,每天8點准時上班,每周三、五去病區查房、會診,每次在病房裡一站就是兩三個小時,每兩周還去一次藥房了解新藥。“每次到例行健康體檢的時候,牟老都催促我們快一點檢查,因為他想趕快回到工作崗位上去。”
“我和患者就像大樹對泥土的情誼。”在牟善初90歲生日上,老人說的這句話讓秘書周桂芳感慨不已。“牟老說自己離不開病人。記得有位患者去世后,家屬反過來安慰牟老不要難過,要他好好保重身體。”晚年的牟善初經常說的一句話是:“在有生之年還能為我的病人做點事,是我最大的安慰。”
在臨床,時間全給病人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治病救人不是索取,更不是交易,知識和技能是人民培養的,解除病人的痛苦是我應盡的責任。”百歲老軍醫牟善初在回憶文章《暮年憶舊》裡的話語鏗鏘有力,“我的座右銘是偉大教育家陶行知曾說過的,‘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成大醫者,必有大愛。
牟善初不僅這樣說,也是這樣踐行的。曾任解放軍總醫院副院長,分管醫療保健工作30多年的趙毅剛,談到牟善初時說道:“牟善初是個‘沒有家’的人!我跟他共事多年,從來沒聽他談過一次家事,從來沒向我提過一次個人要求,從來沒聽他叫過一聲苦。”
在牟善初的二女兒牟小芬眼裡,雙休日裡爸爸極少在家,更別提工作日下班后的時間了,她數不清有多少個深夜爸爸被急救電話叫到病房搶救病患。當記者想看看近期的“全家福”照片時,牟小芬有些無奈地笑著拿出唯一一張上世紀60年代初期拍下的“全家福”。面對記者的不解,牟小芬說:“爸爸除了忙臨床的事,還要帶研究生,好不容易有點空閑,也都用在了圖書館和他的書房。記得有次我生病了,希望爸爸帶我到醫院看病,他說病房剛剛收治了一位病危患者,要去搶救,讓我自己到門診找某某醫生。”牟小芬一點不怪爸爸,只是有些遺憾:“他唯一的一次真正休息是在40多年前,我們全家到北海公園玩,爸爸那天可高興了,可惜沒有照一張‘全家福’照片。現在爸爸可以一直在家陪我們了,但身體卻再不像過去那麼硬朗了……”女兒哽咽了,大家的心也被揪緊了。
“隻有臨床沒有家”的牟善初把時間都給了病人,但他對於病患表達謝意的禮物從來都是拒絕。有位60多歲的新疆維吾爾族老人,患肺部感染並持續哮喘,加之心腎功能不全,十分痛苦,在當地接受抗感染、平喘等治療都沒有效果。家人抱著一線希望打電話向牟善初求救,時已83歲的他二話沒說,冒著臘月嚴寒,兩次飛往新疆診治。經過一個多月的精心治療,病人奇跡般康復了,家人感激地拿出裝有5000元人民幣的信封請牟善初收下。牟善初的回答深深地刻印在老年腎內科副主任醫師劉勝的心裡:“牟老說,‘你們的情義我心領了,但錢我絕對不能收。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職,患者的信任和贊揚就是對醫生的最高獎賞,這比金錢更可貴。’”
生活上極盡簡朴的牟善初至今還穿著帶補丁的襯衣和襪子,但他對待群眾從不吝嗇。早在90年代初,牟善初就拿出5萬元錢為家鄉建希望小學。中國工程院頒發給牟善初15萬元的獎金,他分文未取,全部捐給醫院設立了“牟善初醫療保健科研獎勵基金”,為年輕人的成長進步鋪路架橋……
《 人民日報 》( 2016年12月13日 06 版)
| 相關專題 |
| · 人物事跡 |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